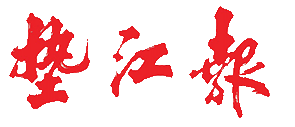曹立中/文
米柜在厨房,书柜在书房,这两个柜子占据着我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角落。日复一日,我掀开米柜的盖子,量米、淘洗,灶上便升腾起温热的水汽。那米柜里盛着的,是一家人的一日三餐,是实实在在的日子。书柜则静立在另一隅,隔着一段距离,却同样与我朝夕相对。作为一个教书人,也作为一个读书人,它的存在,是一种无声的提醒,告诉我精神的世界同样需要粮食,而且一日不可或缺。
我的这个习惯,源于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寒,父亲凭着一点粗糙的木工手艺,叮叮当当地敲打出了两个小木箱。一个放在厨房的墙角,当成了米柜;另一个,则放在了里屋的炕头,权当书柜。它们简陋,甚至有些歪斜,却是我们家里关于温饱与希望的象征。
父亲极其爱惜粮食。每次买米回来,他将米袋口对准米柜,小心地倾倒。偶尔有几粒米跳出角落,散落在地上,他必定立刻蹲下身,用那双布满粗茧的手,极其轻柔地将它们拢到一处,再一粒一粒地拾起,仔细吹去沾上的浮尘,才郑重地放回柜中。那神情,不像在收拾洒落的米粒,倒像在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那一大家子人赖以生存的底气,就都在这个小小的木箱里了。
那时的饭食简单,玉米面、白菜、萝卜是主旋律,吃得我至今见了玉米食品,肠胃还会隐隐地抗议。能吃上一顿纯粹的白米饭,便是无上的幸福。也正因如此,父亲对米柜的守护,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
而在精神食粮同样匮乏的年月,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却从未松懈。他自己不识几个字,却固执地相信书本里有更好的前程。他给我们买来许多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少年文艺》,一摞一摞地塞给我们,没事就命令我们“看去”。他自己则默默地蹲在屋角,点上一支廉价的莫合烟,一口一口地抽。烟雾缭绕里,他不说话,但那不时传来的一两声咳嗽,分明是悬在我们头顶的鞭子,提醒我们收拢心思,不得懈怠。等我们看完了,他又会督促我们把散乱的书册整理齐整,一本不漏地收进那个当作书柜的木箱里。他常说:“东西不值钱,但不能丢。” 在生活上,父亲节俭得近乎吝啬,但在买书这件事上,他从未皱过眉头。
后来,我们兄妹几人相继考学,离开了家。厨房的米柜依旧履行着它的职责,而里屋那个书柜里的小人书和旧课本,却成了父亲排遣思念的寄托。经常听邻居阿姨说,父亲想我们了,就会把那些书搬出来,一本一本地抚平卷角的书页,擦去积落的灰尘。遇到撕破的地方,他会找出胶水,戴上老花镜,极耐心地粘补平整。在那些寂静的午后,摩挲着这些纸张,或许就如同握住了远方儿女的手,能让他感到一丝心安。
我成家后,做了老师,买的书越来越多。后来,屋子里再也堆不下了,我便请了木匠,将书房的一面墙整个打成了顶天立地的书柜。家人的书,孩子的绘本,我的专业书籍,都分门别类地安置进去,整齐,气派,找起来也方便。书柜充实起来,仿佛一种精神上的米柜,也再不会为饥馑而发愁。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他亲手做的那两个简陋木箱,早已在岁月的流转中不知去向。但我每日从米柜中取米,在书柜前驻足,都会想起父亲。是他,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贫瘠的年代,用两个最粗糙的木箱,为我区分了两种食粮,并教会我,对二者都须怀有珍重之心。我今日笔下流淌出的每一个字,根源都在他那里。感谢父亲,不止于养育,更在于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