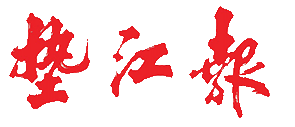徐晟/文
“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布谷鸟的叫声从山梁上滚下来,父亲便知道,芒种到了。
父亲对芒种的敏感,是从骨头里渗出来的。他总说:“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简单的八个字,包含着多少农家的辛劳与期盼。我至今记得他站在田埂上,望着金黄的麦浪时,那黝黑脸上浮现出的复杂神情——既欢喜又忧愁。欢喜的是丰收在望,忧愁的是接下来的劳累。
天还没亮,父亲就起床磨镰了。磨刀石“霍霍”的声音在黎明前的寂静中格外清晰。他磨得很仔细,拇指轻轻刮过刀刃,检验锋利程度。这个动作我见过无数次,却总也学不会。父亲的手掌粗糙得像树皮,布满了老茧和细小的伤口,那是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留下的印记。
太阳刚露头,父亲已经带着镰刀下地了。他弯着腰,左手揽麦,右手挥镰,动作一气呵成。“嚓嚓”的割麦声此起彼伏,像一首单调的歌。父亲的背影像一把拉满的弓,在麦浪中起伏。汗水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淌,浸透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
中午最热的时候,母亲让我给父亲送饭。我提着竹篮,远远就看见父亲独自在麦田里忙碌的身影。走近才发现,他的嘴唇干裂,脸上沾满了麦芒和尘土。见我来了,他直起腰,用袖子抹了把汗,笑着说:“来得正好,肚子正叫唤呢!”我们坐在田埂上吃饭,父亲狼吞虎咽,却不忘把菜里的肉片夹给我。
下午的活更重。父亲要赶在天黑前把割下的麦子运到打谷场。他挑着两大捆麦子,冲担压得弯弯的,青筋在脖子上凸起。我跟在后面捡散落的麦穗,听见父亲沉重的喘息声,心里酸酸的。可父亲从不叫苦,只是偶尔停下来换换肩、捶捶腰,又继续往前走。
打麦是最紧张的活计。父亲说“麦子进了场才算数。”他总盯着天色看,生怕下雨。记得有一次,我们刚把麦子摊开,天边就滚来乌云。父亲像打仗的将军一样,指挥全家人紧急“起场”。雨点砸下来时,最后一捆麦子刚好堆进草棚。父亲站在雨中,浑身湿透却笑得像个孩子。
扬场是父亲最拿手的活。他站在风头,木锨在手中翻飞,麦粒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夕阳给父亲镀上一层金边,他扬场的剪影,成了我记忆中最美的画面。麦粒落地的沙沙声,麦壳飘远的簌簌声,混合着父亲粗重的呼吸,构成了芒种时节特有的交响曲。
晚上回到家,父亲累得连筷子都拿不稳。母亲打来热水给他泡脚,我看到他脚底的水泡和裂口,心疼得想哭。可父亲只是摸摸我的头说:“庄稼人嘛,都是这样过来的。”
新麦入仓后,父亲会特意留一些磨面。第一锅馒头出锅时,满屋子都是麦香。父亲捧着热腾腾的馒头,咬一大口,满足地眯起眼睛:“值了。”这两个字里,包含着多少汗水和期盼啊!
如今,机器轰鸣,田野间已不见父亲忙碌的身影。那些关于芒种的记忆,如同泛黄的照片,被封存在岁月的深处。只是,每年芒种时节,我还会想起父亲,想起他那双粗糙而有力的手,想起他在麦田中挥汗如雨的模样。我想,在那个没有机器的时代,父亲的芒种虽然辛苦,但也一定充满了满足与自豪。因为,那是他用双手创造的生活,那是他与土地之间最真挚的情感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