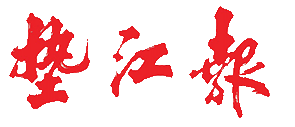朱昭伦/文
小时候在村小读书,特别羡慕那些有书桌的孩子。
在我看来,书桌比油腻的饭桌神圣。从儿时起,书桌就吸引着我去寻找、去皈依。
师范毕业在村子里教书,木工师傅帮找了一张伤痕累累、布满灰尘的桌子做灶台。我舍不得,清洗干净后做了一张书桌。
放学了,学生离开了学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开始在书桌旁用吟诵驱赶寂寞。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人交谈,唯一拥有的是明亮台灯下的一本接着一本的与我邂逅的爱书。我无聊地打开书页,仿佛找到了一群朋友。他们引领我渐渐地走向那未知的领域,文字中那深深的内涵,那独特的魅力,让我无法抵挡。
在那张破旧的书桌上,我读完了20几本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书籍,获得了西南大学的自考文凭。拥有了小学语文教师资格证、初中语文教师资格证、高中语文教师资格证。在这张书桌上,我几乎读遍了能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找到的所有书籍。
后来,我成为了一名中学语文老师。我的野心开始膨胀,在买商品房时想拥有一间书房。房子是步行房三室一厅,经过和妻子的多次沟通争取,虽没有得到一间完整书房,还是在偏小的儿童房里做了一个书架,放了一张书桌。
我是有书房的人了,我的灵魂找到了栖息之地。在这里,我可以肆意地与古人对话,可以穿越时空与异域的灵魂交流。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每一页都是一个新的天地。我在书房中游历,体验着那些我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思考着那些我从未想过的问题。书房,是我与世界对话的场所,是我思考人生、感悟生活的课堂。
过了不惑之年,迈向天命岁月的我突然觉得,垫江如果有一家书院,多好呀?
垫江凤山书院的出现,着实让我心生敬意,让我欣喜不已。我觉得这是垫江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铭记。
自从有了凤山书院,作为一个上班族阅读者,尽管很少去凤山书院,我却始终把它当成我的精神家园。参加了书院的几次公益交流活动,在这个充满智慧和知识的殿堂里,我找到了当教师的最高信仰——“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信仰,它让我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大海中遨游,让我在感动垫江、感动重庆、感动中国的洪流中寻找教育的力量。每一次书院交流都是一次洗礼,每一次书院探究都是一次新生。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在这尘世中,书桌、书房、书院都曾是我灵魂的归宿,也是我信仰的象征。它们承载着我对知识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对未来的希望。
感谢书桌、感谢书房、感谢书院,它们让我找到了自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道路。我将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因为我知道,只有这种信仰,才能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永不迷失。才能真正实现教育者“为而不争”的充盈与丰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