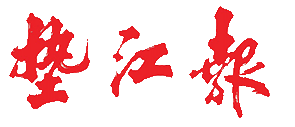孙永云/文
春来万物复苏,惠风和畅。目之所及,那些在山坡,田边及路旁野生的荠菜正油绿鲜嫩,心中倍感亲切。我的野菜情结,不仅是因为它清香味美,更重要的是它参与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父母,虽称得上是庄稼的好把式,但由于家里人多地少,粮食总不够糊口,尤其是到了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那时,母亲总会在忙完家务活后,拿一把镰刀,挎着柳条篮子到地里挖野菜。我小尾巴似的跟在她的身后,看她寻菜,挖菜。那时,最多的好像就是荠菜,母亲说这可是好东西,不但可以作蔬菜食用,还可全草入药,种子含油,供制油及肥皂用。食用时,拌上稀面糊蒸着吃,洗净切碎了包饺子,凉拌等。那时觉得好玩,跟着在地上拔,等到母亲一回头,心疼地惊叫道:“祖宗呀,你拔麦苗干啥?!”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对了菜,母亲又说开白花的不要挖,太老了口感不好。
后来,上百度才知道荠菜只是学名,它有别名叫菱角菜,护生菜等,是十字花科荠属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最高可达50厘米,茎直立基生叶丛生呈莲座状,叶柄长5至40毫米,茎生叶窄,花果期4至6月。宋代诗人许应龙诗云:“拨雪挑来叶转青,自删自煮作杯羹。宝阶香砌何曾识,偏向寒门满地生。”唐代诗人李端也写道:“昨夜天月明,长川寒且清。菊花开欲尽,荠菜泊来生。”可见这荠菜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自古就有了。
那时,最开心的就是和小伙伴一起去挖荠菜了。放学后,扔下书包,抓起挂在窗台上的旧镰刀,风一样旋出院子,朝村北的一大片麦地跑去。那里有一个造纸厂的遗址:一个大烟囱,五六个又大又深的水泥坑,还有一个红砖砌成的水塔。要到那些废墟旁,必须下公路,趟过一大片麦地,然后跳过一个水泥磊的水沟,每当跳水沟时,小伙伴基本上都能跳过去,只有我,心里特着急:水里蓄满了雨水,面上浮着一层绿色的藻,还有青蛙急切的叫声,心想,万一跳不过去,掉水里咋办?万一碰破了膝盖得多疼吗?有好几次,我都观望,也鼓了好几次勇气,但最后都没敢跳,不过,我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的确有几个小伙伴掉进水沟,一身湿,脸上、头上还沾着藻水子。还有一个好玩的就是爬水塔,只要有一个人喊“爬水塔喽”其他的小伙伴都疯跑过去。水塔约十几米高,红砖,上面有一个半圆型瞭望台,周围安装了铁栏杆,要想站到铁栏里远望,得先进到塔内,然后攀着嵌进塔体的铁阶梯,一节一节往上爬。梯与梯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爬前头几个梯子还行,越往上边越难,根本不敢往下看,可想而知,爬水塔我又失败了。我只能站在塔底,听小伙伴们在上边开心的笑声。玩够了,太阳也快没入地平线了,大家这才想起正事来,赶紧挖菜呀,空着篮子回去,轻则会被大人骂一通,若遇到哪家家长心情不好,那就倒霉了,非得挨一顿鞋板子不可。有时候倒也能挖满一篮子,有时候费了很大劲,才装半篮,于是就有人建议,趁地里人少,没人看见,偷一些蒜苗、菜叶啥的垫在篮底,然后再把挖来的野菜铺在面上,并约定,在场的人谁都不许说出去,否则,以后谁也不和他说话。晚饭后,当母亲倒出菜发现“赃物”时,免不了又被她戳着额头狠狠说落一顿,当听到我再三保证,以后再也不偷人家的菜时,她才松了一口气,开始清理菜里的杂草和泥土。
第二天一大早,小小的餐桌上,准有一大碗粉蒸的荠菜,清香扑鼻,引诱着我饥饿的肠胃。许多年过去了,每当在异乡的路边,看到那一株株嫩苗,头顶小小白花,我黯然神伤的同时又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