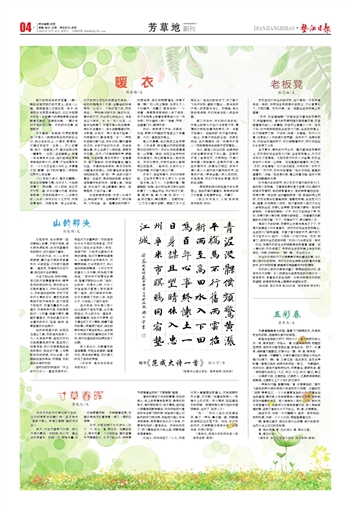傅丽梅/文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落着,一颗一颗碎在桂树刚打的花苞上,击往人心里。距离曾祖父过世已有一年多,记得那日木芙蓉绽得灿烂,这位与党同岁的老人生前最大的遗憾便是没能亲眼看见建党一百周年庆典。一辈子忠诚于党的老人啊!只叹时光无情,徒增感伤。
我家里有一件军装,朴素的橄榄绿,不禁令人联想到英姿飒爽的战士们,挺立在战场上,沙漠中,野草林。它确实来自于一名军人。打从记事起,每次一到曾祖父家,都会出现这样一幅景象:一位老人坐在躺椅上,披着一件洗得有点泛白,但仍能辨出橄榄绿原色的军大衣,很薄,不如说是件风衣;一个小女孩坐在小马扎上,手撑着下巴,眼睛一眨不眨听着老人讲那段烂熟于心的往事:
1937年的冬很冷,雪花似蝴蝶一般在空中肆意飞舞,没过多久,大地就被覆了一层白霜。这个时段,本应家家欢聚一堂,孩子们嬉戏欢闹,却被战争毁掉!我那时刚满十六,从没想过敌人会深入到我们这个三家村,然而世事难料。我跟往常一样上山砍柴,邻家的阿毛尾巴似的跟在我身后,一路叽叽喳喳笑个不停,给静谧的林间带来一丝活力。夕阳欲落之际,变故陡生:一声枪响划破天际,响彻长空。意识到不对,我让阿毛待在山上,独自往山下奔去。“爹,爹?”无人应答。心脏开始刺痛了,我捏紧拳头抵住痛源,寻找还活着的人,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没敢掉,爹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推开门,眼泪滑落,“爹!”一声吼叫自嗓子眼飞出,我扑过去,颤抖着伸手过去,爹的尸体已然冰凉。我呆呆跪坐着,手上沾满了父亲的血,满是茫然无措。突然,门外响起脚步声,踢踏踢踏,如在刨雪,是日本鬼子!他看着我,搔了搔脑袋,我狠狠瞪着他,瞳孔充血。我看到他举起枪,黑漆漆的枪口瞄准我的额心,我盯着他的食指缓缓扣向扳机,“砰”的一声,他的太阳穴冒出一朵血花,身体倒向地面,食指还维持着开枪的动作。随着心脏一阵痉挛,我也倒下,闭上眼睛前,瞧见一抹橄榄绿,之后不省人事。
爹在前面使劲跑,我怎么也追不上,唤他停下来。他果真停了,转过身来,七窍流血。血一直蔓延到我脚下,我想后退,却似被荆棘缠住,动弹不得。“啊!”我从床上弹起,如溺水之人大口喘气。“你醒了,感觉如何?”一个穿着一身橄榄绿军装的人走了进来,我才发现身上披着件橄榄色大衣。“我爹呢?村子里的人呢?”“抱歉,节哀。”他望着门外,眼神死寂。
我们一起拼凑了尸体,没再说一句话,默默为村里的死难者立了块墓碑。大衣一直披在我身上。
第二天清晨,他们连的卫生员带来一个好消息:昨日屠杀村民的那群鬼子已如数歼灭!我们心中的悲痛得到一丝慰藉。随后,他和卫生员护送我去避难处,阿毛跟着其他人前去抗日。我本也想去,然而天生的心脏病是位拦路虎。一路走过,也有好几个村庄被屠,我们皆为其立了碑。
夜深了,怕出现意外,我们没有赶路。卫生员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些干柴,生了火。火舌舞动着,“噼里啪啦”地响,他们开始讲红军长征的故事了。“从瑞金开始,我们走过了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十一个省,吃过雪水,啃过草根......”他感叹说:“二万五千里长征啊!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在他们的叙述下,我了解了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感受到共产党人的艰苦与决心。我相信,有这样的党领导,我们定能将敌人赶出中国。
第二天中午,我们到达目的地。我身上的军大衣始终没有脱下来,薄薄的衣服抵住凛冽的寒风,我一点都不觉得冷。他临走时,我才猛然惊觉,一路上,我竟不知他的名姓。我赶忙问他,他只摆摆手,说:“我是共产党人!”两抹橄榄绿渐渐隐于茫茫雪地......
如今,曾祖父已经过世,他常讲的这段往事却刻在了我心里。正是共产党人舍身忘死,不畏艰险,才得以有中国人民的解放;正是共产党人提出改革开放,创建经济特区,深圳才得以有从小渔村向大都市的改变;正是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攻坚克难,我们才有如此幸福,和平的生活啊!
一束和煦的阳光照在窗外的木芙蓉上,洁白花瓣闪着星光,橄榄绿的军大衣挂着,彩虹高悬半空。天晴了!
(垫江中学高三.三班 傅丽梅 指导教师:邬玲)